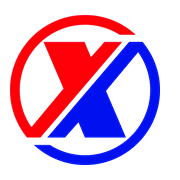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宮略》 - 【宮略】第119章

☆、120第119章
「給萬歲爺請安。」蘭草蹲了個福道,「我們主子……」
皇帝抬了抬手,示意她不必說。待人都退下了方去敲門,放柔了聲氣兒喚她,「素以……禮貴人,貴人主子,是我,開門吶!」
他在欞子上敲,在門框上敲,在裙板上敲,一聲聲敲在她心上似的。素以坐在一片黑暗裡,窗口洩進來的一點微光照在鏡子上,她看見自己早已經淚流滿面。
什麼叫愛恨交織?大概這就是了。她折磨他也折磨自己,就是那種恨得牙根癢癢,越痛越解氣的感覺。她不能叫他好過,她這陣子受到的委屈也要讓他嘗嘗。
皇帝敲門敲得很耐心,篤篤聲不絕於耳,「我知道你沒睡,你也別擔心伺候不了我,我不用你伺候,我能料理好自己。你開開門,難道不想我麼?我可天天念著你呢,快叫我看看你……素以,別使性子,聽話。」
他還嫌她使性子?把她擱在慶壽堂不聞不問,且不說她懷著身子,為什麼病了都不來瞧一眼?她不是那種非要爺們兒常伴左右的人,可那麼些天,說人在江南倒罷了,明明離得很,走兩步就能夠著的,一點兒音訊都沒有算怎麼回事?沒錯兒,她在慶壽堂錦衣玉食有人伺候,但那種時不時冒出來的被丟棄的感覺,真拿什麼都填補不回來了。
他不停的敲門,敲得人無比煩躁。她努力克制著,捂起耳朵伏在梳妝台上,可惜不能阻隔,心跳的聲音伴著嗡嗡的血潮,愈發催生出她的反感。想他的時候他不在,現在她不需要他了又來糾纏。她不想見他,也害怕見他。她枕在臂彎上,眼淚打濕了中衣的衣袖。她該怎麼好呢?愛情惹不起,這場男女間的博弈,陷得深的人注定被動。她一直以為自己很自持很冷靜,其實她的那點信心都源於確定他愛她。現在渺渺茫茫看不清了,她慌了神,覺得一下子失去那麼多。尊嚴像潑在地上的水,再也拾擄不起來了。
皇帝的敲門聲漸急,用的力也更大了,把屋子都敲得隆隆作響。他耐著性子耗了半天,她完全不為所動,他真有些生氣了。她以前不是這樣的,懷了孕就變得這麼奇怪,到底為什麼?她在御前做過女官,他忙起來日夜顛倒她也見到過,那時還能聽到一句暖心窩子的話,現在怎麼不能理解他呢?他是皇帝,為國家大事操勞是他肩上卸不下來的擔子。他沒有皇父的福氣,有老莊親王這樣的兄弟扶持著。太上皇十三個兒子十個不成器,不是走雞鬥狗就是種花看女人,剩下一個老十三是好苗子,但是年紀畢竟太小,也幫不上什麼忙。他做阿哥時是辦事阿哥,做皇帝還是個辦事皇帝,她也不是今天才認識他的,怪他冷落她他可以賠罪,這樣閉門不見是什麼意思?
「素以,你開開門,有話當著面說,藏頭露尾不是個英雄。」他氣極了,高聲道,「你只當一扇門板能攔得住我?你再不開門,我可要踢門進來了。」
素以聽了發毛,哽著氣道,「你踢,踢在我肚子上才好呢!」
她回敬他這麼一句,頓時讓他偃旗息鼓了。她善於拿捏他的痛處,穴位上輕輕一點就正中他的命門。他束手無策,靠著牆根低語,「你要我怎麼樣?這幾天我忙得腳不著地,顧念不上委實疏忽了你。我對不起你,讓你大著肚子孤零零的,是我沒想周全。早知道把你接進養心殿多好,我又瞻前顧後怕你太勞累,橫豎左右都不是。你別這樣,有什麼不舒心的和我說,你想什麼要什麼也和我說。求你別和自己過不去,你肚子裡還有孩子,氣壞了你們母子我也沒法活了。」
素以又紅了眼眶,他說得好聽,大概一切都是為了阿哥。皇后打孩子的主意他不知道麼?他說了什麼?也是,祖宗家法不能荒廢,他這麼清正的人,容不得在史書上留下半點詬病。這些她都明白,即便心裡不捨也願意諒解。佳偶之時以心換心,待得成了怨偶,那就處處要費神挑眼了。
實在是乏累得厲害,她扶額平了平心氣兒。自己是急性子,其實很想一股腦兒倒出來,可急火攻心太傷身,況且扯嗓子一通翻扯不解氣,也太便宜他了。她長長一歎,緩聲道,「主子,奴才今兒確實乏了,也沒想好拿什麼臉子面對您。萬一三句話不對鬧起來,大家心裡都不痛快。您先回去,有什麼事兒咱們以後再說,成不成?」
「你這是唱哪出?」皇帝真急了眼,「就是死也讓人死個明白,你這麼躲著不見是長遠的方兒?開門,聽見沒有?」
素以也惱了,摸到梳妝台上的象牙如意就朝門砸過去,咚的一聲響,牙彫落在地上頓時斷成了兩截。
她不說話,門外也緘默下來。這時候的煎熬是最難忍受的,她咬唇止住哭,細聽外面的動靜,悄然無聲,大概他也被唬住了吧!她扶著椅背想起身,卻發現腿彎子沒了力氣,怎麼也站不起來了。
「你真叫我難堪,素以。」隔了半晌皇帝才道,「我花了那麼多的心思,誰知都是無用功。我這輩子除了你,沒有愛過別的女人。過去二十八年白活了,所以做得不夠盡善盡美,哪裡不好你指出來,我一樣一樣的改還不成麼?可你為什麼要這樣?」他吸口氣,覺得心肺一寸寸冷下來,「我知道你恨我困住你,讓你這麼勉為其難,是我太自私了,我也後悔。早知道給不了你要的日子,我就不該耽誤你……你見我一面,有什麼氣衝我撒,千萬別憋壞了自己。」
他在門前站著,像個被遺棄的孩子。明間裡高燃的羊油蠟嗶啵作響,照亮他肩頭的團龍繡花,照不亮他心底枯敗的一隅。他把手撐在門上,恍惚以為她來拔門栓了,再用力推推,紋絲不動,不由無限惆悵,原來只是他的錯覺。他感到心力交瘁,昨夜折子批到三更鼓響,稍合了一會兒眼天光就放亮了,論乏累,誰能比他更甚?他抬手想再拍,舉了一半又放下了。步步錦隔心上了大紅漆,菱花邊沿上描金,一圈一圈讓人眼花繚亂。他垂下雙手呆呆站了一陣,也不知怎麼,他說,「今兒不見,明兒也不見了嗎?我等你半柱香,你開門,咱們什麼都好商量。要是不開……我以後再也不會來了。」
聽面傳出嗚咽的哭聲,她說,「你想知道原因去問長滿壽,叫他一五一十的告訴你。我進宮四個月,經歷的事兒比過去七年都多。我心裡有你,遇上點溝坎能忍得。你興頭過了撒手,我認了命守著空院子也能忍得,可你不能叫我吃啞巴虧……你走,我同你無話可說。趕緊的走,我惱起來砸東西,砸完了我瞧了要心疼的。所以你快走,別攛掇我糟蹋擺設!」
她嗚哩嗚哩說了一通,語速又快,皇帝隔著門沒聽出頭緒來。再要問她,寢宮裡又是一片死寂,石沉大海一樣沒有回音了。
他滿臉淒苦,垮肩站著像失了線的偶人。皇帝又怎麼樣,在她這裡照樣不受待見。她趕他走,只差沒讓他滾了,這是多大的怨恨?他腦仁兒痛得刀絞一樣,抬手摸摸竟都是虛汗。踉蹌退後一步,隨侍的太監上來扶他,被他回手叫退了。自己轉身往外走,邁出門檻,空氣裡的一點微涼迎面撲來,把先頭那些酒勁沖淡了,心思也漸漸清明起來。
廊廡下跪了一地的人,長滿壽迎上來給他披斗篷,輕聲道,「主子息怒,禮主兒心裡有委屈,先前在老虎洞那兒都和奴才說了。您瞧她這會兒道乏,誰勸也沒用。奴才先伺候您回養心殿,您今兒偏勞,先適適意意歇著,容奴才慢慢向您回稟。」
皇帝回頭看了眼,南窗裡面黑洞洞的,滴水下的西瓜燈搖曳著,照亮玻璃後面隨窗掛的山水簾子。看來是有內情的,但是怎麼不同他說呢?因為怨他,再不願意和他說話了嗎?原本最親密的人,到最後鬧得這樣生疏……
他上了九龍輿,說不出的懊喪難以排解,進了養心門還是昏沉沉的。他這個壽星翁,撂下一攤子賓客自己躲起來避世,說來真有些禮數不周。但是管不了那麼多了,他進門站在殿中央,榮壽弓著身腰上來替他解氅衣。這奴才先頭往自己臉上招呼過,兩頰有些腫,加上一雙水泡眼,看著臉架子有些變形。
長滿壽在一旁侍立,覷一眼皇帝,欲言又止。
皇帝捲著袖子坐到案後,面前一盞奶茶熱氣升騰,模糊了他的視線。他捏了捏眉心,倚著圍子道,「說吧。」
榮壽一驚,也不知道皇帝是對誰說話。想起先頭慧秀回來討主意,料著萬歲爺是知道了什麼,恐怕要現開發了。他嚥了口唾沫,一頭是實情,一頭又忌諱罪名不大壓不住皇后,如果兩頭得罪,那日子更不好受。兜兜轉轉的計較,越計較越心驚。瞧長滿壽耷拉著眼皮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,自己真得好好琢磨怎麼應付了。
正打算來個裝聾作啞,二總管不緊不慢接了口,「回萬歲爺的話,禮主子今天這通發作,原不是沒有道理的。剛才坤寧宮外她打發人傳奴才,還沒開口,就哭得止都止不住。萬歲爺啊,奴才看了都揪心,好好的主兒,還大著肚子,您瞧……」
皇帝急起來,他話說半截叫他大為惱火。往扶手上一拍,寒聲道,「你再賣關子,朕叫人拉你出去點天燈!還不一氣兒說完?」
「庶。」長滿壽口氣是慼慼焉,眼神滿不是這麼回事。得意的乜斜了大總管一下子,這小子像霜打了似的,快蔫兒了。他心裡痛快,模樣卻十足苦大仇深,哀著嗓子道,「是這麼回事,您忙政務,小主兒天天記掛著您,知道您愛吃小餃兒,上回特地命小廚房做了,冒著雨送到養心殿來。可那回不湊巧得很,榮大總管把她攔在抱廈裡不叫進殿,後來慧秀出來,說您歇著午覺……小主兒想了,您辛苦,見不著就見不著吧!打算回去了,誰知道裡頭小太監說您正找慧秀呢,小主兒一聽就難受了,您醒著不見她,叫她怎麼想?」他嘬嘴咋舌,「這是一宗。第二宗,小主兒前幾天病得厲害,連著發燒,把人都燒糊塗了。小主跟前宮女怕阿哥爺出事兒,過乾清宮來求鴻雁兒傳話,說主子這麼些天的沒一點兒消息,興許是忙忘了也不打緊。可這回小主兒病得危及,何況肚子裡還有龍種,好歹求您過去瞧一瞧。結果等了您三天,沒見您露面,這下傷透小主心了,在慶壽堂哭得淚人兒也似。要說多大的事兒,真沒有,也就是您顧不過來,小主心又窄,鬧了這麼個局面。不過話又說回來,女人懷身子時候想得多,就愛讓男人捧著。您是萬聖之尊自然不比外頭爺們兒,可十來天就見鴻雁兒傳一回話,小主兒可不要胡思亂想了麼!」
皇帝聽這拉雜一套,起先還沒別清楚,耐下性子來,榮壽後面的解釋簡直讓他覺得不可思議。好些情況他都是頭回聽說,什麼時候不願意見她,怎麼又叫十天就見鴻雁兒一面?他分明派他天天過去請安的,就算有示下說沒要緊事兒不必回,鴻雁兒問吉祥也不能短。這倒好,敢情十來天壓根兒就沒辦過皇差?
他怒不可遏,「叫鴻雁兒進來。」
鴻雁兒得了令,從甬道牙子上一溜小跑進來。才開宴那會兒禮貴人進乾清宮,她丫頭問那天的話傳沒傳到,他就知道壞了菜了。慧秀這丫頭坑他,這是要把他往死路上逼啊!他嚇破了膽,進了門跪地膝行到御前,扒著磚縫磕頭,邊磕頭邊篩糠,「主子叫奴才……奴才在,奴才是個笨王八,不用主子問,奴才自己說……初五那天奴才是答應給蘭草傳話來著,因著主子上昌平巡視水利沒在宮裡,奴才就懈怠了。恰逢那天奴才師傅身上不好,奴才晚間又不上值,慧秀姑娘黃鼠狼好心眼兒給奴才遞話兒,奴才怕耽誤了口信兒就答應了。沒想到主子入夜迴鑾,第二天奴才要回稟,是慧秀說她同主子說了,奴才一時嘴懶也沒細問就含糊過去了……奴才是個吃草料的牲口,這身賤皮子欠收拾……求主子恕罪,奴才再不敢了……」
皇帝聽明白鴻雁兒的話,也不言聲,轉頭打量這位御前女官,眼神刀子似的插在人頭頂上。
熏香爐子邊上侍立的慧秀漲紅了臉,膝頭子一軟便跪拜下來,「主子明鑒,奴才初五壓根就沒見著鴻雁兒,他這是脫不了罪找替死鬼兒呢,奴才冤枉死了,求主子給奴才做主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