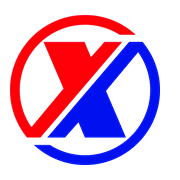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淫唐傳》 - 【淫唐傳】第153章

風醉夜唐。頑獸李元吉篇
風醉夜唐
頑獸。李元吉
給自己的二十一歲生日禮物
李家的三兄弟,個性南轅北轍。李家長子審慎、端嚴、守禮;二子開朗外向,運籌帷幄;略過早亡的三子,李家的四子,被兩個哥哥的鋒芒所蔽,卻在另一極端上找到屬於他的光茫。李家四子李元吉暴戾而乖僻,身上都是灑脫不掉的少年人的張狂。說起這人,無人不聞風喪膽。
這樣的個性,似乎不適合當身為太原李閥的嫡出兒子。李家人不寵愛元吉是人所共知的事,雖然同住一個家裡,但那種隔閡與冷漠,顯然得連身為外人的我都看得出來。這對李元吉來說,或許是好事。沒有人管他、理他,他就可以儘管揮霍他年少的張狂。而他也不負眾人所望,既是沒人管,就壞事做盡。連養娘也會狠心打死的人,對他來說,殺人傷人乃家常便飯。李家長輩罵也罵過,教也教過,教不好,就更是放任。
而對於這個弟弟,李世民一向也很少提及,然而,他雙眼從沒少留意過他。每次當元吉闖禍回來,李世民的眼神當中,總少不了一種高高在上的鄙陋。
「陛下不喜歡他?」
那天我在庭園裡,看見李世民倚在欄邊,一付好整以暇,遠遠看著從李淵房裡氣衝衝跑出來的李元吉猶如隔岸觀火,又見到他眉眼裡掛著那種鄙夷。我這樣問他,他脣角當下添了一分笑意,悠悠告訴我一聲「不喜歡」。
他口裡說不喜歡,那眉眼卻笑得深了,漸漸到了一種深不可測的地步。深不可測,但其實我皇的心意,又哪裡是我能猜測出來的。
於是我也托著腦袋,看他遠望那邊廂怒氣沖天的李元吉,自得其樂。
李元吉曾說能三天不吃飯,不能一天不打獵。李世民也喜歡打獵,不過兩人的手法,不盡相同。打獵時的李元吉投入奔放,他會化身成獸,像不要命地追捕獵物。齊王打獵何止用箭,他更愛使槊,挨近獵物直接捅死它們,近距離感受獵物死前的痛楚。李世民則永遠會處於高位,他冷靜沉實,絕不喪失身為人類的理智,往往會使弓箭。總之直至他拾起獵物之前,雙手一定不會有血污。
那天我隨李家出外打獵,山間蹦出一頭毛色潔白如雪的雄鹿。李元吉搶先駕馬衝前,沒入林中前不忘回頭望瞭望李世民,給了個挑釁的目光。我本以為李世民會跟著去,與他一決高下,卻見他立在原地不動,臉上是那一貫的蔑視之色,而當中,卻透露出了一種掩不住的悅樂。他就這樣白白看著李元吉追上雄鹿,舞槊與它近身角力,看著李元吉在雪鹿身上劃開數道口子,毫不忌憚地任鮮血染污了雪白珍貴的皮毛。
我見李世民動也不動,不禁問他:「你就由得他贏你?」
李世民好像沉醉在什麼似的忽然猛醒。眉目一閃,他朗然一笑:「憑他?怎麼可能!」
他就面帶那種寵溺而滿懷心事的笑,策馬去了。大弓一滿,矢箭脫弦,無差無誤地插入雪鹿的心胸位置。雪鹿後腿猛蹬,一命嗚呼,李元吉眼見自己吃到嘴邊的獵物被搶,當下臉死如灰,什麼心情也沒有,打獵才進行到一半就走了。李世民什麼都沒說,就這樣看著他走,而臉上笑意不減,彷彿這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
當夜,李世民就帶著這雪鹿的鮮剝皮毛來到齊王府,無視李元吉的逐客令,就展著那張皮毛,直接走進了他房裡。我在房外,聽到他這樣說:「四弟好像很喜歡這雪鹿,為兄的特意把皮毛送給你的。怎樣,喜歡嗎?」
不料李元吉未等他說完就抄起茶壺揮向那皮毛上,嘩啦一聲,皮毛本就滿是槊孔與鹿血,現在加上茶印,想必會變得更是狼藉。李元吉乾脆一手扯下那皮毛,直接揪住李世民的衣領:「李世民,不要給我假惺惺的!你就想逞想威風,想挫敗我,但我告訴你,上天不會永遠偏愛於你的,我李元吉……」
話到這裡就沒了。然後房內一片嘈鬧,誰摔破了杯子,呯呯磅磅的,接著燈火滅了,室內一片漆黑。我倚在門邊,只能依稀聽見粗重的呼吸聲,過了好一會,寂靜中終於爆發出元吉的惡罵。
「雜種!!你這天殺的……!!狗娘養的……」
李元吉罵得越來越毒辣,我卻聽見當中有李世民微弱的笑聲。及後李世民幾乎是被李元吉摔出門外,他人不慌不忙地站好,整理衣冠,這才緩緩轉身面向關住的門,又帶著那臉優越而自滿的表情,朗聲長笑。
我用猜的,把房裡的事猜了個大概,然後腦裡就蹦出了一個詞。
──貓捉耗子。
不久,李世民果然完成了他身為貓的本份,搭上了元吉的妻子,耍得李元吉暴跳如雷。妻子事少,面子事大。李世民似乎最清楚元吉的弱點在哪裡,也最清楚知道他最痛恨自己所餘不多的尊嚴被折。最後元吉為了輓回面子,投向了太子黨,聯同李建成一起攻擊李世民。
如此兄弟相殘的局面,居然恰恰是李世民想見到的。他每天應對著太子黨,忙不迭之間,卻看出當中有不少享受的意味。
直至那夜太子黨給李世民喂了藥,讓他半死回來,我終於不禁多口透露:「陛下,當心逼虎跳墻。」
對於我難得多言透露的歷史,李世民卻像是聽到了童言童話那般笑了出聲,還一副理所當然地反問我:「就憑他嗎?沒錯,他頂多,就是狼虎之流。」
見他眼裡又泛起那片自傲的目光,真龍天子之相形日露。我稍有不安,不自覺喃喃低語:「陛下既知李元吉凶如猛獸,那麼鹿死誰手,有待分曉。」
李世民冷哼一聲,臉上的優越稍為收斂了一下,轉迅就變回那種高高在上的神色,他雙脣動了又動,執著「就憑他嗎?」這句問話,一邊來回斟酌,一邊心不在焉地在長安城的地圖上圈圈畫畫,把玄武門的圖示,圈了四五六次。
於是玄武門一戰在李世民眼裡,變成了一場盛大的涉獵。撇開當時的政治因素,兄弟間的權位之爭,生死之鬥,這誠然就是一場涉獵。
涉獵些什麼,到底是皇位、權財,還是些別的什麼,則恐怕只有李世民才知道。
混亂之中,李世民的馬被流箭所傷,跑入林裡,李元吉將他擒住。李元吉騎在他身上,欲以弓弦絞殺他。弓弦深深陷進世民的頸喉,我看見他臉都變色了,卻仍放不下臉上那蔑視的神色。那神色就像看透世情般超然。他痛苦萬分,卻仍死心不息地,對李元吉喚了一聲「四弟」,然後,慢慢的說了一句話。
「……你難道,就一直以為我恨著你?」
李元吉聽罷,先是一楞,轉瞬雙手便似被些什麼觸發了般。他狂叫一聲,發了狠地絞著弓弦,只望李世民沒快點死掉。突然背後一發冷箭自林後射出,直直射中了李元吉的背心。李世民看見他的下屬舉著弓在他面前,說是護駕。李世民竟沒喜沒悅,也沒驚沒愕,就這樣一臉空白地看著李元吉吐血在他身上,倒到自己懷中,痛苦地抽搐,直至斷氣過去。他好不容易,伸出了手來偷偷在李元吉背上撫了一下,然後眉宇上那種一貫看著李元吉時的高傲終於釋下。
「你真的不喜歡他嗎?」
戰後我這樣問他,李世民已沒直接回答我。以後,他娶了李元吉的妻子,殺了他的子嗣,一切像無痕無跡,什麼都從未發生過那般。李世民半倚在宮裡朱紅色的欄柵上,那姿勢像他那天懶洋洋地倚著身子看望園中的李元吉,只是此時,臉上那種半是鄙薄半是自滿的笑意,已不復見。
「知否馴獸者如何馴化不知人性的獸?」
他忽然這樣問。我稍為想了想,漫不經心地說:「自是以獎賞與懲罰去誘導。」
「獸不知人性,何來賞罰?」
「那該當如何?」
「只有一個法子,就是不斷地摧折它,讓它知道誰才是主人。」
我不禁笑了:「那豈非只有懲罰?我的陛下,強權高壓,可不是明君該依行的。」
「你錯了,這不是懲罰。在沒有做對與做錯的情況下,這根本不能算是懲罰。再者,既是沒有人性,那麼是賞是罰,都沒有分別了吧。」
李世民極目遠望,喋喋無休,似是自圓其說。只是他眼之所及,已沒了那可讓他興奮自滿的身影。
「沒有人性……世上可真有全然沒性之獸?」
他聽到我這樣說,就止住了說話,赫然發現眼下是一片連綿的宮墻,都已然屬於他。李世民不喜反愁,他如是回答我:「……只有沒有人性,才會懵懂不知,世上也有愛他的人。」
(李元吉篇。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