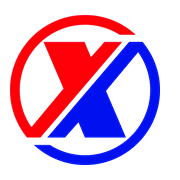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宮略》 - 【宮略】第103章

☆、第103章
南方的氣候和北方不同,入了二月天氣開始回暖,河堤上柳枝抽了新芽,燕又南飛。偶然的停留,能咂出別樣秀麗婉約的味道。
連著奔波一個月,到了蘇州府沒住客棧,包了個民居安頓下來。江南的建築有別於京城,四面樓,采光只靠天井。人站在底下抬頭望,屋宇就顯得尤其高深。皇帝閒暇時愛坐在搖椅裡看天,真正四四方方的一塊,襯著白牆黑瓦當,天藍得要朝你洶湧撲過來似的。陽光明媚固然好,下雨天也很不賴。雨絲兒細密如牛毛,順著光看是一縷縷的,不急不躁,紛紛揚揚,還未到廊下,就四外飛散了。只是南方濕冷,初春的雨帶出一大片寒意,在外面呆久了心尖會發涼。
這種時候最想她,不知道她在幹什麼。也許在臨窗讀書,也許在和丫頭玩翻紅繩。再想得旖旎點兒,或者學了個新花樣,在燈下繡肚兜也說不定……
江南魚米之鄉,普通百姓的日子十分悠閒。這座宅子對面是間茶樓,靜下來的時候能聽見裡頭悠揚的二胡琵琶。吳儂軟語低吟淺唱,雖不知道在唱些什麼,光聽吐字也很有意思。
可惜了祥和之下總有暗湧,江南織造的官匠們怨聲載道,查清原委是這趟南下的要務,所以得在這一片多停留陣子。原本計劃兩個月的行程怕是不夠用了,隨扈的都是男人,宅子裡不雇老媽子打點也不行。富奇頭子活絡,買人不可能,就在附近的民宅徵集。短工,出的價又高,自然有人願意幹。都是農婦麼,憨直不知道拐彎,拿了你的佣金很好套話,從她們嘴裡能打聽出點當地民生來。
她們沒做慣奴才,僱主面前也剎不住,仍舊大剌剌的。皇帝站在簷下,看她們在細雨裡的井台邊上淘米。其中一個挨過去頂另一個的肩,聲氣兒低低的,帶了點察言觀色,「噯,統點銅鈿來呢1。」
另一個扭過頭來一瞥,「倷門檻精咯,我袋袋裡相一塌刮子兩隻銅板,倷要麼拿去2。」
皇帝一頭霧水,只看見前頭說話那個臉上訕訕的。這時候腰門上進來個送菜的男人,擔子往烏盆邊上一擱,嘖嘖讚歎著,「哦,格只缸窮大個嘛3!」
皇帝看他們交談覺得有意思,送菜的似乎和呲達人那個是一家子,兩個人轉開了唧唧噥噥說私房話,自討沒趣的婆娘把手裡抹布一扔,轉身往灶間去了。
在外面站了有會子了,榮壽過來打千兒,「主子回屋裡用碗油茶吧!這兒寒氣往骨頭縫裡鑽,沒得凍著了。剛入的春,傷風了不容易好。」
皇帝聽了慢慢挪步子,還記掛著織造局的造冊,問榮壽,「景從孝回來沒有?」
榮壽說沒有,話音才落,看見門上進來個筆帖式打扮的人。背上插面小旗,跑得滿面塵色,估摸著是從北京日夜兼程而來。到門禁上見了侍衛,掏出一封油布包裹的折子往上呈獻。侍衛接了快步過來交皇帝御覽,皇帝起先倒不覺有什麼,料著大約又是京裡的請安折子。打開來逐行的看,看到三阿哥薨那裡,頭嗡的一聲就大了。似乎是轉不過彎來,愣了一陣回過神,頓時痛得要窒息似的。
萬歲爺臉色慘白,這可嚇壞了榮壽和一幫子隨扈的軍機們。萬歲爺不言聲,他們又不好問,個個眼巴巴的等他開口。皇帝沒有說話的力道,把折子遞給了大學士顧行。軍機們傳閱了,這樣的噩耗實在是讓人痛心,顧行歎息道,「萬歲爺保重聖躬,人死不能復生,一切還需從長計議。」
皇帝擺了擺手,「這裡的事就交給你們了,榮壽備馬,朕這就回京去。」
他只是想不通,三阿哥的死怎麼會和素以有關,兜兜轉轉還牽扯上了皇后。看來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,她過得並不輕鬆。
在馬上顛簸,靠著四條馬腿一里一里的跑,心裡熱油煎似的只恨太慢。腦子裡千般想頭,揣測了各種可能,他知道她的品性,她不是那種蛇蠍心腸的女人。折子上說得不詳細,單寫了個大概的經過,說三阿哥誤食了禮貴人的點心,究竟這點心是不是和皇后有關,還在盤查。
他想得腦仁兒都木了,慶幸素以平安無事,可死的是他的三阿哥,也足以叫他肝腸寸斷。他是冷面君王,他不苟言笑,但是他的拳拳愛子之心不比任何一個父親少。做了皇帝,七情六慾不外露,這是人君的體面。他唯有咬著牙日夜兼程,到一個驛站換一匹馬,連著三天三夜沒有合眼。然而路太遠,馬背上喝水馬背上啃窩頭,緊趕慢趕,仍舊只趕了歸程的一半。
以前他不知道,他一直以為他的後宮平安寧靜,即使有長短計較,也不過是女人之間的小打小鬧,不會鬧出人命案子來。原來他錯了,他對素以的寵愛成了導火索,他低估了女人的妒忌心。他的枕邊人裡,也有勇於奪人性命的好手。可惜了他的兒子,他的毓敏。養到六歲大,已經知道心疼父親的好孩子。
從蘇州府到北京,不眠不休跑了七晝夜。回到宮裡時看到烏泱泱跪著請罪的人,他頭一回感到心力交瘁。三阿哥停靈在欽安殿十八天了,他進了殿裡,眼前模糊得看不清那口小小的棺槨,只聽見耳邊嗡嗡的哭聲,遠的近的,層層疊疊,像翻滾的水浪。
他走過去撫撫漆棺上的仙人紋,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克制著沒有哭出來。緩了會子吩咐莊親王按貝勒的規制下葬,沒有再停留,回身便往長春宮去了。
好些不清不楚的事兒也要求證,他傳了弘宛過來,得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。
皇后身子弱,這陣子折騰下來一副病歪歪的樣子。看見他進門趕緊下炕蹲福,抬起頭來,眼淚成串的往下掉,哽咽著,「你到底回來了……」
皇帝好言安撫一番,扶她到圈椅裡坐下,聽她把來龍去脈說一遍,方轉過頭來問鄭親王,「眼下查得怎麼樣了?」
鄭親王道,「奇得很,那天各處當值的太監都篩查過了,愣是沒找著禮貴人說的那一個。要說會不會出了宮,咱們連宮門上的進出宮記檔都翻找過,又讓禮貴人身邊宮女認人,可認來認去都對不上號……」
皇帝拉了臉子,「你們辦差真叫朕瞧著眼暈,宮裡幾千太監,你讓她們認,人能從兩個眼睛一張嘴超脫出去嗎?她們就是見過那個太監,當時一霎眼辰光能記得住?幾千個鼻子幾千雙眼,擱在你面前叫你認,你倒是認一個給朕瞧瞧?糊塗!」大喝一聲把他兄弟喝得矮下去半個身子,他氣得喘了兩口氣,看他們這十幾天的進展也知道他們辦事不力。畢竟查太監是治標,宮裡的主兒們只能外圍打探,這一大片動不得,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。他忖了忖又道,「叫畫師來,照著她們說的樣子畫畫像,不說全像,畫個七八分也能找出些眉目來。慎行司幹什麼吃的?你們內務府、宗人府又是幹什麼吃的?單查當值太監,保不住不當值的也出來溜躂。眼下有個笨法子,叫闔宮太監到太和殿前頭天街上去,首領太監們給朕拿著花名冊子一個一個的對臉點名頭,看看有缺的沒有。幹了這樣的事,九成是不敢在宮裡了。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,除非是叫人滅了口,否則沒有找不著的道理。」
鄭親王應個庶,退後一步看皇帝在地心來來回回兜圈子,他嚥了口唾沫道,「其實這案子看著破綻百出,可真要問出個原委來,實在是難。禮貴人身邊宮女傳了很多回,到最後貴人都不叫她們出慶壽堂了。她又是有了身子的人,咱們拿她也沒轍……」
皇帝聽了這話愕然回頭看皇后,「素以有喜信兒了?」
皇后擦擦眼點頭,「沒錯兒,有了,都快兩個月了。我正要告訴你呢,這回的事兒把她委屈壞了。她是直性子的人,伺候你那麼久,你也知道。你前腳走後腳就鬧這麼一出,她又不是沒聖眷的人,何至於幹這麼傻的事兒?她和三阿哥沒仇怨,害了他對她也沒好處。依著我,你們最該查的就是那些有兒子的人。沒有念想的人記掛什麼?只有有所出的才怕她受寵,怕她生兒子搶了她們兒子的風頭麼!」
皇后這話有些武斷,但是細琢磨也不是沒道理。皇帝按捺著狂喜看了鄭親王一眼,「你才剛的話沒說完,接著說。」
鄭親王道是,「臣弟這話可能不中聽,可是……禮貴人說她是在夾道裡接著食盒的,當時正值各宮主兒給皇后娘娘問了安散伙,照理說看見的人很多,可臣等逐個的問宮眷們,卻一個作證的都沒有……既這麼,臣斗膽猜測,這事兒會不會是禮貴人自己……為的是要……」話說半截,眼梢兒往皇后那兒一瞥,意思很明白,禮貴人就是這起案子的始作俑者。害了一位皇嗣,再繞進去一位皇后,如果她野心夠大,這就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。
皇后緘默下來,這種可能她不是沒想過,鄭親王這個疑問提得是時候,正好探探皇帝的立場。她蹙起眉頭有意無意的撇清關係,「素以不是這樣的人吧!我一心一意待她,她斷不會對不起我的。不過要說那點心,真不是我這兒賞出去的。那天小廚房的廚子不在,抽冷子說我送的東西,真叫我愣住了。至於說沒人作證,那天靜嬪不是還搭訕來著麼!」
鄭親王摸了摸鼻子,「話是這麼說,可轉天再問她,她說那天染了風寒說胡話,當不得准……」
皇帝白了鄭親王一眼,「虧得沒叫你掌管大理寺,否則冤案大概得堆成山了。沒人作證是因為牆倒眾人推,這都尋思不通?皇后常賞她吃食,她要成心往皇后頭上扣屎盆子,非得挑個廚子不在的時候叫人抓著把柄?」他厭惡的回回手,「狗屁不通,朕瞧你光認得你們家那顆石榴樹了!照著朕說的好好查,再查不出,你這內務府總理大臣也不用當了。去吧!」
鄭親王被一通罵,明白了禮貴人的封號不是白得的。這是疼到心眼子裡頭去了,但凡萬歲爺他認為不能的事兒,自然能也不能了。還有什麼可說的?麻溜回去辦差吧!鄭親王掃袖請了個跪安,卻行退到殿外去了。
皇后早料到皇帝是這麼個反應,她也不覺得奇怪,橫豎她只要孩子,旁的一概不問。
她挪過去,「瞧你臉色不好,這一路奔波累壞了吧?是在我這兒歇,還是上素以那兒去?我知道她心裡不受用,遇著這麼大的事兒,又懷著孩子,正是要你安慰的時候。我讓人備了熱水,看你這一身的土,換洗好了再過慶壽堂,啊?」
皇帝想想也好,沒的把路上沾染的病氣兒帶進她屋子裡去。
皇后摘了手上護甲,伺候他進後殿更衣。邊給他脫馬褂邊切切道,「你不知道,聽說素以懷了孩子,我真高興壞了。你曉得我的心願,前兩天懿嬪的五阿哥落地,我也上心來著。可孩子身底子不好,又太小,暫且留在親媽身邊更受照應,我也就沒打發人去抱。素以這一胎我可盼了好久了。你們後頭可以再生,這個得記在我名下,你答應麼?」
其實這原本就是祖制,皇后打不打招呼,結果都一樣。皇帝略一擰眉道,「記在你名下,對孩子的前途有好處。可朕怕素以難過,到底是頭一個,情分不同一般。」
皇后拿皂角給他洗頭,慢吞吞道,「這一胎要是一舉得男,晉個位分就是了,少說也得是個嬪。當然了,都瞧著你,你願意晉妃,也不是不能夠。位分高了才有換養孩子的資格,下頭再生個老七,她願意自己留著,我睜隻眼閉只眼,不也過去了麼!」
皇帝把毛巾搭在額頭上,乏累道,「現在不是說這話的時候,才剛懷上就計較這個,也忒讓人寒心了。」他掬捧熱水擦擦臉,心裡惦記著往慶壽堂去,打發皇后道,「朕自己來,你身上不好回去躺著吧,我換了衣裳就過去。」
皇后有些失落,皇帝沒立時答應她叫她心裡沒底。易子而教是南苑起就有的規矩,總不至於到這一代就改了。皇后垂著兩手直起腰來,靜靜站一陣,覺得自己委實有點操之過急。這是把孩子當貓狗,還在肚子裡就謀劃討要,對生母來說的確是不大厚道。不過也不打緊,有劉嬤嬤在,素以總不能躲起來生,早晚還是打她手上過。到時候瞧準了抱到長春宮來,皇帝不好較真,事情也就塵埃落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