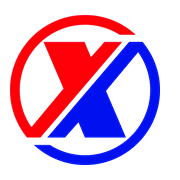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悖論 - 親姐弟》 - 《悖論【親姐弟】》晦暗分界

這一晚很疲倦,按道理凌思南應該沉沉睡去。
可是不知道為什麽,就算眼睛闔上,大腦依然清醒。
她就在這種半夢半醒中迷迷糊糊不知道過了多久,直到東方的天空翻出魚肚白,沒有拉緊的窗簾露出一絲光線打進這個漆黑一片的房間裡,她突然就睜開了眼睛。
被褥和皮膚摩擦的窸窣聲響。
她盯著天花板,全身骨頭裡遊走著散了架的酸。
雨水拍落在玻璃上,外面還在下雨,天陰。
腦袋好悶。
就是……有點分不清虛幻還是真實的躁悶。
披散的長發從枕上被攏起到肩頭,她怔怔地坐了會兒,也看了一會兒窗外的雨。
整個世界在雨幕中都是朦朦朧朧的,一如她的思緒。
隨手拿起一件衣服,她披上肩,起身走出了房間。
走廊盡頭,客廳的時鍾顯示早上5點。
夏天清晨的5點,因為這場雨變得晦暗難明。
陽台上側倚一個人影。
肩背筆挺,身形修長,側面的線條可以看到喉結突出的曲線——那一瞬間她突然有個錯覺,站在那裡的是一個男人,而不是一個少年。
天還是灰蒙蒙的,所以他手上淺淺呼吸的星火尤為清晰,有青色的煙氣自那點紅光向四周散去。
凌思南蹙起眉頭,快步走了過去。
拉開陽台的落地窗,他恰好轉頭,下一秒手上的煙就被她搶下。
煙已經燃了大半,她氣鼓鼓地將剩下的煙頭丟地上,就著拖鞋踩熄。
凌清遠安靜望著她,眼中的琥珀依舊淡泊。
好像剛才那支煙並不是從他手上被奪過去。
她很生氣,氣得呼吸都有點不穩:“什麽時候學的抽煙?覺得有意思嗎?”
他定定地看了她兩秒鍾,忽然笑了。
“沒抽。”他說。
凌思南更氣了:“你還睜眼說瞎話?”
“真的沒抽,姐姐。”凌清遠一手搭著欄杆,朝她微微俯身,瞬時拉近的距離。
然後唇覆了上來。
許是在陽台站了一段時間,薄唇微涼。
含著她的唇瓣,輕吮了一下,又一下。
清茶的香味,再無其他。
退開了些許,抵著她的唇際,悄聲泄露了笑意:“現在信了嗎?”
十二樓真高啊。
凌思南暈乎乎地想。
她捂著砰砰作亂的心口,下意識回頭看屋內。
“我把他攙回房間了。”凌清遠抬手攏了攏她的衣襟。
“別轉移話題。”凌思南還是不太愉快地屈起起手指敲他額頭,“沒事點什麽煙,裝什麽帥呢?再讓我看到你玩這個,我就……”
他故作可憐地摸摸被敲的腦門,挑眉問:“就什麽?不理我?”
“……對。”想不出來別的。
他傾著身笑,“你不舍得,何況我又沒有真的抽。”
她還想說話,凌清遠倒是先解釋起來:“幾年前確實想過,但是抽了兩口就戒了。”
……抽了兩口你好意思用“戒”這個字啊。
“那時候他們跟我說抽煙緩解壓力還特別男人,可是那味道真的糟糕透頂,不適合我。”凌清遠說,“我沒有憑抽煙這個行為增加自己成熟度的必要。不過,看煙燃燒的過程堵對我來說很舒壓——即便只是一點火星,也能緩慢燃盡一支煙,像是溫水煮青蛙,積累久了……總會有變化。”
他眺望遠方雨中飛翔的群鳥,扇動著翅膀在大雨中翱翔。
“姐姐。”
“我想最後再問你一次——對於他們,你真的決定好了?”
凌思南走前一步,搭上欄杆,“你覺得我應該學著去原諒他們嗎?畢竟我是他們的孩子。”
凌清遠不置可否。
“其實這不是設問句。”凌思南微微攥了攥指尖,“就像是孩子不能因為是孩子作惡就沒關系,父母也不能因為是父母犯錯就無所謂——大家都是來這個世上過那麽一輩子,何況他們也沒有真心養過我,憑什麽我就要讓著他們?”
她閉上眼,感受著空氣中的濕意撲在眼瞼,那一刻水珠似乎在眼角凝結。
“你還是別期待他們‘真心’養你吧。”凌清遠笑了笑,“我就是他們‘真心’的結果。”
“——兩年以前,除了睡覺吃飯的時間,我都在讀書。”他偏頭,試圖回憶,“只會讀書還不夠,還有各種課外班需要學,如果我反抗,等待我的就是禁閉室——沒有按時做完卷子,連飯都不會有。”
凌思南有些意外,她以為父母對清遠至少應該是百般呵護的,至少在吃穿上不會有任何的怠慢。
凌清遠大概察覺到了姐姐眼中的驚訝,有些無奈地問:“你是不是也以為我沒被打過?”
凌思南更詫異了。
“受到壓迫總會有反抗,有段時間我反抗得太厲害,他生意又不是那麽順遂,經常喝了酒打我。”嘴角嘲諷地翹了翹,“最初的導火索是那一天,他發現我養了一隻狗。”
凌思南想到弟弟日記本裡的那幅簡筆畫。
“他把它扔了出去,然後拿皮帶抽我。”說這些事的時候,他的目光無波無瀾,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情緒毫不在乎,“那時土豆——我養的那隻狗,隔著門狂吠,大概是把他惹怒了,他衝出去也抽了它幾下——估計土豆還不到一歲吧,就是一隻小狗,哪裡挨得了幾鞭子。”
凌思南搭上弟弟的手背。
“我拉著他也打,不知什麽時候土豆爬起來咬住了他的褲腿,他踹它它也不走——其實那時候我是想讓它走的,走了就不要回來。”
走了,就不要回來。
“後來……”凌清遠頓了頓,“他把它丟到了排汙的窖井裡。”
凌思南的心跟著緊了一瞬。
“本來就受了傷,也叫不了幾聲……再之後就什麽都聽不見了。”他慢慢地垂首,把頭靠上姐姐的頸窩,聲音發悶。
她攬過來,輕撫他後腦泛棕的發。
“你知道嗎?他們早就安排好了我的人生。”凌清遠的聲音從她頸間浮起:“我該有什麽愛好,以後上什麽學校,要讀什麽專業,在哪裡工作,幾歲適合結婚,和哪家的女兒結婚最好……我和土豆的不同,就是不會被丟到窖井裡。”
他活在一個光鮮亮麗的窖井。
只會更慢性地窒息。
“你現在看到的一切,是因為我改變了。”
如果改變不了他們,就改變自己。
表面上,他不再反抗。
但憎怨,有時候就像默默燃燒的煙。
一旦點燃,最終會有灼手的那一刻。
“我只希望,你不會變成我這樣。”
雨聲淅瀝。
良久,耳邊傳來她恬靜的聲音——
“你並沒有很糟糕,別這樣看輕自己。”
凌清遠抬起頭。
“你很好。”她說。
“不然,我又怎麽會喜歡你?”
他低笑了一聲。
“別笑,我說認真的。”她窘迫道。
“我知道。”聲線輕磁,他吻了她一下,“我知道你是認真地喜歡我。”
“啊你好煩。”凌思南撇開眼睛不敢看他,把話題拉遠,“你怎麽一直不問我,為什麽答應和沈昱訂婚?也不問我打算怎麽辦?”
話題轉變之快讓凌清遠楞了一秒。
“我從來沒懷疑過你會不會和他在一起,姐姐。”他說,“我知道你也在為我努力。”
天光亮了,外面逐漸光亮的世界,讓身後的房間像是陷入了黑暗的深沉裡。
凌清遠又一次攏好她披在身上的衣襟:“回去穿好吧,今天……穿暖和點。”
“啊?”她笑,“你才是,別淋濕了。”
她拉起他,牽著手走到拉門邊。
想起什麽。
“謝謝。”
有很多東西需要感謝。
謝謝他相信她。
謝謝他作為弟弟。
謝謝他作為戀人。
她抬手,勾下他的後頸,主動送上了綿長的吻。
一吻極盡溫柔,像是空山雨後揚起的風,像是盛夏蒼穹包容的海。
與光同行,只因有你。
相擁已經不夠傳遞熱度,輾轉不休的吻交換著彼此的口津。
直到她氣喘籲籲地睜開眼,意識到必須就此打住,才飛快推開他走進了客廳。
屋裡尚且有些暗。
不知道為什麽,大概是冥冥之中的直覺,她下意識看了一眼玄關。
玄關明暗的分界裡,不知何時,多了一雙女士鞋。
抬頭的那一刹那,她站在那兒。
昏暗裡。
一瞬也不瞬地。
望著他們。
眼中的,是深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