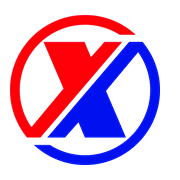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鐘琪回憶錄[NP]》 - 【鐘琪回憶錄】第65章

分手
二審判决沒有下來,鐘琪可以居所看管。
換好賀秋陽帶來的衣服,鐘琪出去時,薛渡臨等在門外,見到她便一巴掌拍上她腦門,一語雙關的:「看守所也敢進,鐘小琪你能耐了!」
鐘琪斜了他一眼,轉頭去看他身後。薛渡臨朝天翻了個白眼,悄無聲息地側開身體,讓她看個够。
江聿城背靠著墻壁,燈光打在他輪廓深刻的側臉上,投出小片蒙昧的暗影,西裝革履的模樣,有一點深沉。
算一算好久沒有再見他,看守所裡不覺得,碰了面竟然會升起一點微妙的感慨。
鐘琪扣好腕間的錶帶,笑著問他:「秋陽應該告訴了你來龍去脉,怎麽今天還是來了?」
江聿城偏頭看她一眼,米色的高領毛衣、淺藍色牛仔褲,流連在肩窩的黑色碎發,身上的顔色稍顯寡淡,倒是很好地遮住了她的瘦。
他不發一語地邁開長腿,鐘琪稍稍頓住動作,正好賀秋陽過來,低聲和她說最近的情况,她收回落在江聿城背影上的目光,低下頭和他交談起來。
外面還有記者,鐘琪一行人繞開他們,徑自去了停車場。
賀秋陽拉開車門,鐘琪正要上去,江聿城突然抓住她的手臂,不由分說地把她塞進自己車裡。
鐘琪的目光掠過打火的江聿城,他沒什麽表情地踩下油門,車子轟隆一聲駛離。
她思考了陣,問他:「江先生這是?」
回答她的是一車厢的沉默。
到了別墅,江聿城對傭人說:「去放熱水。」
傭人看他臉色不是很好,再看他身後的鐘琪,小心地去樓上放水。等到大廳裡安靜下來,江聿城沉沉地坐進沙發,緘默地抽起烟。
片刻,江聿城深黑的眼光滑向玄關,鐘琪正彎著腰換鞋,他低聲說:「鐘琪。」
鐘琪停下動作,抬眼看他,「嗯?」
「一審之前,我們通過很多次電話。」江聿城熄滅烟蒂,「爲什麽沒告訴我孫家要起訴你的事。」
鐘琪有片刻的怔忪,隨後她笑出了聲。
這件事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告訴江聿城的理由,現在倒是讓他發了火。
……她男人脾氣還真大。
「我知道江先生擔心我。」鐘琪裸著脚踩過地板,走到沙發那兒,單膝跪在他身側,一隻手繞過江聿城的肩扶住靠背,「不過他們沒有贏的機會,這件事就沒有告訴你的必要。」
「我不這麽覺得。」江聿城伸臂攬住她的腰,手指從她的毛衣下擺探進,仔細地摩挲她的肋骨,「開始的時候我和你說的很清楚,我以爲我們兩個不是在開玩笑。」
鐘琪:「在說這句話之前,你應該想到,我沒有問過你回新加坡具體要做什麽,你也沒有對我彙報的念頭。」
江聿城:「這兩件事沒有可比性,你和我不干涉對方是尊重,可如果某件事有風險,在做之前,我會選擇明明白白的告訴你。」
他收回手,再將她的下擺整理好,沉聲說:「但你不會。」
鐘琪:「如果是你說的情况,我會。」
「你確定?」江聿城翻開外套,慢條斯理地從口袋裡拿出白色的手套:「那我怎麽不記得你對我說過,你做了白手套?」
傅家。
老爺子躺在搖椅上,闔著眼聽跟班說:「……案子重審,這一次丘悅做爲關鍵證人被保護起來。老爺子,我和幾個公檢方碰過,一個和我們交情不錯的透露——」
跟班食指朝上指了指,「——注意到這件事了。」
老爺子長久地沒有回應,搖椅晃動,輕微的咯吱聲中,他突兀地咳了幾聲,跟班急忙彎下腰去扶他。
「丘悅、上市、輿論、二審……」老爺子抬手格開跟班,緩了緩氣,徐徐睜開眼,「這一環環一扣扣,都是她的算計啊。」
「他會注意,不就是她的目的?她想讓全國的人看見我,用公衆壓力讓上頭對我下手,想來一招借刀殺人。」他摩挲著光滑的把手,像是在和跟班說話,更像自言自語:「那丫頭看我快要退休,就以爲我沒力氣再動,還是以爲想給我定罪,只憑一個女人的幾句話就行?」
老爺子拿起拐杖,慢慢地扶著把手坐起,「不管怎麽說,她倒是逼著我不能再留下孫家。」
他猛烈地再次咳嗽起來,眼光却轉向角落裡跪著的孫子。
聽著撕心裂肺的咳嗽,傅崢嶸啞聲說:「爺,事情已經鬧大了,您老停了吧。」
老爺子徹底被他氣到,他抬手將拐杖丟出去,眼看拐杖砸到傅崢嶸的額頭,那裡可見地破開道口子,滲出一點血色來,「你、你偷偷跑回來、就是爲了和那丫頭一起氣我?」
「那丫頭、她和傅家是死仇……」老爺子捂著心口,喘著氣說:「你那點子心思她瞧得上?沒骨氣的東西,被人利用還斷不了心思,你給我滾出帝京,一年之內不准回來!」
傅崢嶸眼皮沒抬,動也不動。
老爺子真的老了。
他由始自終沒有瞧得起鐘琪,不相信一個女人真的能撼動到他,甚至是傅家。
那他怎麽能想到,上頭會注意這事,也許不止是因爲輿論。
更不會想到,他大概沒有還手之力。
「這時候上市不是在融資,是在送江山。能讓上頭收下,你給的恐怕超過一半。從此之後,你和政圈挂了鈎,天上吹什麽風,你就是什麽情形。如果風向不對,第一個死的就是你。」江聿城抬手捏住她的下巴,嗓音裡透著冷:「我不問你是誰的手套,只問你這件事的風險够不够大、該不該說,嗯?」
……看來是江聿城動了真火。
鐘琪:「應該。」
她手指搭上江聿城的手背,輕輕捏了捏,一股子安撫的意味:「澳丹對於你和鐘氏對於我幷不能劃等號,我不在乎那座大厦——」
「對,你不在乎。」江聿城打斷她的話,「你只在乎能不能討回邵家的債。」
鐘琪幾不可查地淡了表情,「江先生。」
「我又戳到你的痛處了?」江聿城輕輕晃動她的下巴,「他是你的老師,也是你的責任。」
他的長指穿過她的鬢髮,讓她眼尾的疤現了出來,「爲了他,你什麽都可以不要,就算他死了十年。」
「江聿城,」鐘琪垂下眼,「死人該得到尊重。」
江聿城抬起深眸。
四目交接,各自風雪涌動。
江聿城忽而自嘲地笑了聲,「鐘琪,你捫心自問,你和邵衍在一起的時候,和你跟我一起的時候是一樣的態度?」
不是被感性操控的年輕人,能把保有底綫的親密關係維持的很好,然而這一次的事情真真切切地讓江聿城看見了她的潜意識。
江聿城起身拎起外套,慢條斯理地穿上,「回來之前我讓傭人熱了飯,等會兒你吃一點。」
鐘琪坐到沙發上,伸手去摸桌上的烟盒。餘光看見江聿城走到門口,她問他:「你確定你要走?」
「總得有一個人走。」江聿城扣上外套紐扣,回頭看見她點了烟,他說:「鐘琪,當時在c城你就明白,我能接受最壞的結果,是你——」
他喉嚨滾動,嗓音微啞:「沒有和我走到最後的打算。」
本來他以爲,彼此對局面有絕對的掌控力,有眼光有能力,可以確定那一種選擇是最好的,就不需要其他人來指手畫脚、指點江山,自負都是同一種模樣,很多事不需要多說。
結果這不過是疏離的一種形式。
她不曾把最深層的大門對人敞開過。
那後面住著一個人,還有她荒蕪的十年,她所有的悸動和柔軟都在那兒。
而他不可能贏過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