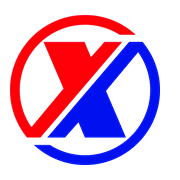《高幹之不清不楚[NP]》 - 【高幹之不清不楚】第28章

028
但總有人會嫉妒,誰沒看得出來林鸞鸞到底有甚麽個本事,能將首長給套得牢牢,不就是有個年輕的身體,年輕的身體,世上多的是,又不獨她林鸞鸞一個。大概說是權力是春藥,這種春藥,不光對男人有用,對女人更具有吸引力。
秦鄆的妹妹秦曼莉到是早早地看上了高培德,可惜高培德是個睜眼瞎,沒看到她,被個小妖精似的林鸞鸞給收走——
但秦曼莉必是不服氣,她哪裡缺了?還真是哪樣兒不缺。
國內排名第一流的學府畢業,又到國外進修過一輪回來,一回國就給安排了工作,她本身也是個願意往上走的人,心氣兒也高,進了商務部,如今說出來也算得是個頭面人物了。
她哥是秦鄆,不是甚麽不上牌面的人,而是牌面兒太上了。
誰都知道秦鄆是高培德的下一任,這麽著吧,奉承秦曼莉的人就多了去,不管老的少的,爲了顯示自個兒與秦曼莉關係熟,就統統的都稱她一聲「姐」。秦曼莉到是享受這個,面上到沒露一點兒,還帶著幾分嬌矜的姿態,將人都往眼底看。
她尋思著那小妖精幾年沒露面,怕是叫首長給厭了,沒曾想,這小妖精又不知道打哪裡冒出來,又在她面前露眼,——本是首長與忠臣良將們的聚餐,彼此更近一步的交流「感情」,秦曼莉越看越覺著林鸞鸞這個小妖精是個多餘的人。
桌上坐的都是頭面人物,她呢,就小妖精一個,想方變法地榨著首長的精血呢,才這麽一想,秦曼莉桌子底下的腿兒巴巴地就夾緊了些,首長那物事,她到是見過——滋味沒嘗過,到是想嘗,首長沒讓她近過身。
想著如今首長在個小妖精的身上耕耘,那一身的精血都灌給了小妖精,秦曼莉這心上的火就越大,她的眼神兒直勾勾的,也不怕別人個發現,就盯著首長看——沒一眼給小妖精林鸞鸞的。
她了喝酒,是特供的酒,這酒香極醇,香得她的臉頰都飛起了紅暈。她站起來,端著酒杯向著首長道:「首長,我敬您一杯。」
她身段兒極好,找不出一點兒缺點,豐胸肥臀,還有細腰兒,身上雖穿著幷不顯眼的套裝,可那套裝做得貼身,將她的好身段顯了個十足十——
特別她說話的姿態,真個是眼神含春。
秦鄆這臉色就有些不好看了,但他沒失態,他慢慢地看向小夫人,見小夫人姿態極正地坐在那裡,好像沒瞧見有人對她丈夫獻殷勤,——小夫人的面,他見過,秦鄆冷不丁地握緊了酒杯,當年,他與首長同時中了藥……
才這麽一想,他覺得腿間一緊,褲子都緊綳了些。
他眼神晦澀,沒敢再瞧小夫人第二眼。
他是個孬種。
隻敢將東西往人家肚子裡捅,倒不敢真將人往家裡帶,首長到是有風骨,真將人帶回家,真把人給娶了入門,真真個正經的小夫人。
高培德沒起身,這桌子上的人都沒敢出個聲。
這桌上的都是高培德的心腹,自是知道高培德的心思,首長的眼裡只有小夫人,不管秦曼莉什麽的,都不足以入他的眼底。
高培德沒起身,到是小夫人慢慢地有了動作,她笑著瞧了高培德一眼,「老高呀,人家給你敬酒,你都不吱個聲,叫人家姑娘家怎麽下得來台?」
高培德朝她一笑,充滿了縱容。
小夫人拿起酒杯,李成濟就替她倒了酒,紅色的酒液在杯光閃著璀璨的光芒,映著她晶亮的眼睛上,朝著秦曼莉道:「老高最近身體不好,我不讓他喝酒了。既是敬酒,我就代他喝了?」
秦曼莉還是看著高培德。
高培德看著小妻子,朝在坐的各位說道:「鸞鸞就愛管著我,我昨兒個早上醒來就要抽烟,剛一咳嗽,她就不讓我抽烟,不光不給抽烟,還不給喝酒。」
說著,他還舉起酒杯,笑著說:「爲了不掃大家的興兒,我這裡也像模像樣了倒了點兒白開水,她說呀,要是誰敬酒,就她來喝。她年紀小,不經事兒,就疼我……」
這話說的在坐的人都心一驚,本就不敢小看林鸞鸞,這會兒更不敢小看了,都說男人通過征服世界征服女人,那麽女人就是通過征服男人來征服世界,——別看著林鸞鸞年紀小,可她實實在在是因著高培德,成了被衆人仰望的存在。
高培德這話在場的人都是人精,誰都聽得出來。
所以林鸞鸞端著酒杯子,一口就喝了,將個杯子反著拿,一杯酒都沒有,她臉上帶著笑意,「大家都別拘著。」
秦曼莉憋著一口氣,就將酒喝了,她從來沒覺得酒苦過,這一回,她覺得這酒香沒了,到是苦得很,苦得她整個人都難受。
她一輩子沒跟別人低過頭,一連兩次都被迫倒在林鸞鸞身前。
她還是笑著接話道:「小夫人您可真疼首長,疼得好。」
高培德看向小妻子,拉拉她滑嫩的小手,笑著與大家說:「既是大家都在,我也不妨把話擺在這裡,她是我妻子,你們待我,也要一樣兒待她。」
這就是表忠心的時刻,大家都齊齊地站起來,包括滿心不是滋味的秦鄆兄妹倆都在,他們兄妹倆各懷心思,到也跟著大家齊齊地表忠心。
但高培德得了林鸞鸞一記別有意味的眼神,那眼神含著媚態,——叫他的心懸得高高的,他特別的期待。
果然,這回去,林鸞鸞讓他去洗澡。
吃完澡,他自是光著出來,都老夫老妻,沒必要掩飾。
他平時也很注重身體,雖沒有肌肉累累,畢竟他精力擺在那裡,幷不能再跟年輕人似的練個八塊腹肌出來,到是也沒瞧著有什麽贅肉,瞧著清清爽爽一男人。
但林鸞鸞擺出了架式,身上就披著朱紅色的睡袍,襯得她個白晰的身子更顯白膩嫩滑,——睡袍特別的輕薄,依稀能看得見睡袍下的身子隱隱若現,胸前的柔軟布料讓微突起的莓果子給頂起來。
她坐在床邊,笑看著他。
纖纖的手,她指了指床。
高培德懂了,這是叫他躺著。
偏她綳著張俏臉,一點笑意兒都沒有。
是生氣了?
高培德自是聽話,就真的往床裡一躺,不爭氣的孽根,見著她的模樣,早就疼得腫脹,就這麽一躺,孽根就大赤赤地矗立著,瞧著挺可怕。
她到是好,矮了身,脫了自己身上的睡袍,一絲不挂的站在床前,一條腿往床裡跨一步,就用睡袍這位首長綁住雙手,——而首長呢,一點都不反抗,反而是由著她鬧,任由她綁著雙手,跟個祭品似的。
林鸞鸞綳著臉,「不許動。」
高培德聽她的話,到是爲自己小小兒地辯解一下,「我沒碰過她……」
語氣還清白無辜。
林鸞鸞那自然是遷怒了,「她甚麽個人?」
她跨坐在他肚腹間,就是不肯將就在那孽根上,任由著那孽根貼在她後臀處,火熱滾燙,「你平時對她是不是笑過了?是不是安撫過她了?」
高培德失笑,「哪裡能,我眼裡只有你一個人。」
可林鸞鸞撅了嘴,「她敢當著你的面,大家的面這麽就挑釁我,誰給她的膽子?」她不懷好意地瞧著他,——回頭看著抵在她後臀處興奮的幾乎顫抖的孽根,大拇指的指腹就按住最上頭蘑菇狀之處,眼見著最中間有個小眼兒還興奮地溢出一絲白濁來。